Abstract:
The core idea of occupational health risk assessment models is to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occupational health risks according to target hazard characteristics and relevant exposure levels of workers. Occupational exposure assessment is based on concentration, frequency, exposure time, and other indicators that indicate actual exposure of workers to occupational hazards, which is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health risk assessment. However, the accuracy and comparability of assessment results are affected by differences in parameter assignment for exposure assessment across different studies, as well as insufficient emphasis on multiple occupational hazard exposure. This review aimed to explore the assignment and standardization of exposure assessment parameters for occupational health risk assessment modeling, and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the meaning, assignment methods, and sources of exposure assessment related parameters in commonly used occupational health risk assessment models, with the goal of providing researchers with standardized assessment tools to enhance the scientific rigor and practicality of occupational health risk assessments. Considering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temporal fluctuations in occupational exposur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researchers should adopt appropriate sampling strategies, reasonably select sample subjects and time based on the division of similar exposure group (SEG), and conduct statistical inference on the obtained data to derive representative exposure parameters. For combined exposure to chemicals with similar toxic effects, the health risk assessment methods are relatively mature. However, the assessment of combined exposure to hazards with different properties and health effects still lacks scientific authority and needs further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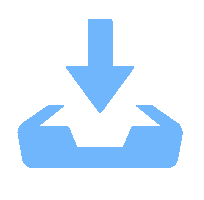 下载:
下载: